卡尔·楚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楚曼是格罗夫城市大学(Grove City College)的教授,著有《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文化失忆症、表现型个人主义和性革命之路》(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等书,他为传统基督徒提出了介于当前美国基督徒中极端的“觉醒的迎合主义”(woke accommodationism)和粗鲁的特朗普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我可以把这第三条路称为“忠心的现实主义”: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神学和文化中保持严格的正统性,虽然我们在这样做时应该以一种文明的方式,但我们不应该指望观看我们的世俗世界会为我们的这些正统神学而鼓掌。
楚曼在“第一要务”(First Things)的一篇长文中解释了他的第三种方式,题目是“福音派精英的失败”("The Failure of Evangelical Elites"),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我非常鼓励大家阅读。这篇文章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在这里我重点讨论与我最相关的部分:他对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和乔治·马斯登(George M. Marsden,我在圣母大学读博时的导师)的著作和思想的评论: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为恢复和捍卫正统基督徒的智识和学术诚信做出了持续努力。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历史学家乐马克和乔治·马斯登,他们勇敢地主张基督徒要成为有智识之人。在《福音派心智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一书中,乐马可认为美国的福音派因为过度委身于一些缺乏智识可信度的立场而饱受束缚。因此,福音派遭到教会外受过高等教育之人的蔑视。更糟糕的是,反智主义和智识缺乏使教会内有思想深度的人过的艰难。乐马可把注意力集中在时代论和按着字面相信六天创造的年轻地球论上,认为这些观点在理性的准则下都站不住脚,也不是相信正统基督教所必须的。
《福音派心智的丑闻》是一本畅销书,并被《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评为年度图书,《今日基督教》可是福音派的旗舰杂志,其目的便是希望基督信仰在捍卫正统教义的同时避免过度极端的基要主义。此后不久,马斯登在名为《基督教学术令人发指的想法》(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的著作中论证了他的想法。他的论证中历史的部分基于他早先发表的关于许多美国顶尖高等院校基督教起源的研究。马斯登的结论是,当反对和鄙视基督信仰的精英人士声称信仰使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他的智识和学术抵触时,他们是完全错误的。在他论证的建设性部分,马斯登认为,基督教学术界可以在不损害信仰正统性的前提下,培养对学术准则的谨慎尊重,并与同行其他学者进行深思熟虑的真诚接触。
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不同,乐马可和马斯登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对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充分肯定。同样与施莱尔马赫不同,我觉得他们的论点很有说服力。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死和身体复活的信仰并没有破坏智识的严谨或损害学术标准——当然,除非这些标准从一开始就反对基督教义。但毫无疑问的是,乐马可和马斯登的观点之所以受到特别积极的欢迎,是因为199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福音派人士想要确认自己的信仰并不反智——因为他们就读的大学越来越多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信仰不符合理性和学术要求。乐马可和马斯登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表明,一个信靠基督之人只要愿意自我批判、摒弃信仰中反智的观点,仍然可以充分参与现代学术生活。
尽管马斯登和乐马可在不到三十年前就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论点属于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回想起来,那种认为致力于诚实和正直的学术研究可以使一个人获得今天的大学和其他主要研究机构成员资格的想法是幼稚的。今天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觉醒者”的地盘。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或者对米诺斯文明有深刻的了解,但如果他在种族、性、甚至代词使用等主流文化上有任何偏离都会在招聘和任职过程中遭到冷落,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比学术能力和仔细研究等因素更重要。
楚曼指出,当他在格罗夫城教授马斯登的著作时,学生们发现马斯登的论证很有吸引力,但有些不切实际,这都是因为目前精英学术界和企业文化的不宽容情绪。
我认为楚曼说到点子上了,而且我确实发现乐马可和马斯登的论点听起来越来越像上一代人的东西。我还想说,他们的福音派和基要主义立场及历史学术成果,对我来说仍然是精辟和历史研究方法的黄金标准,现在看来也(可悲的是)有点过时了。他们的作品虽然批判了福音派,但同时也对福音派有同情心。过去十年中最流行的福音派历史反而是以积极反福音派的模式写成的。在对美国福音派的研究中,厌恶往往取代了同情,甚至在一些基督教历史学家中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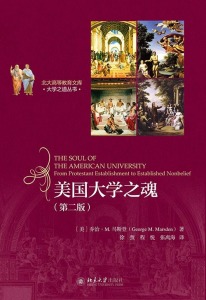 然而,马斯登也对现代学术界提出了批评,这一点楚曼没有完全解释(当然,就这一点就可以写一篇长文章了!)。在《基督教学术令人发指的想法》和《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中,马斯登挑战现代世俗学术界要对其宣称的后现代主义和多样性负责任。他认为,如果我们都承认每个人都有其文化视角,如果一个更有活力的学术界需要包括一系列不同的视角和经验,那么为什么要把直言不讳的基督徒排除在学术界之外?为什么基督徒(或其他传统信仰的人,如犹太人)不应该有“一席之地”?马斯登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意识到,学术“多样性”通常并不真正具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然而,马斯登也对现代学术界提出了批评,这一点楚曼没有完全解释(当然,就这一点就可以写一篇长文章了!)。在《基督教学术令人发指的想法》和《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中,马斯登挑战现代世俗学术界要对其宣称的后现代主义和多样性负责任。他认为,如果我们都承认每个人都有其文化视角,如果一个更有活力的学术界需要包括一系列不同的视角和经验,那么为什么要把直言不讳的基督徒排除在学术界之外?为什么基督徒(或其他传统信仰的人,如犹太人)不应该有“一席之地”?马斯登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意识到,学术“多样性”通常并不真正具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一个短暂时刻,马斯登对意识形态多元化一致性的呼吁似乎有机会在精英学术界为更多的基督教观点腾出空间。他本人因为写了即批判又称赞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传记而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研究奖(the 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这可以说是颁给美国学术派历史学家最负盛名的奖项。我无法想象一个基督教历史学家今天会因为这样一本书而获得如此褒奖。
此外,在21世纪初,贝勒大学的“2012愿景”开始了。贝勒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同时保持对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明确认信,至少是一种宽泛的认信。这一愿景的命运是另一个话题,但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的领导层变动,以及贝勒可怕的橄榄球队性侵丑闻,肯定没有能够帮助贝勒保持住整个高校的信仰焦点乃至信誉,特别是在其对基督信仰委身这件事上。
楚曼提出,在学术界获得精英认可需要神学上和道德上的努力,需要基督徒在圣经研究、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各个领域都付上努力。然而,我仍然不相信传统基督徒与精英学术界之间是像楚曼所说的那样黑白分明的。(有人可能期待我作为马斯登的学生说点与楚曼不同的想法)毕竟,楚曼本人在一所优秀的基督教学院任教,按照通常的世俗学术标准这间学校也相当不错,而且他还在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内的精英学术机构出版过著作。他作为一个基督教学者不可否认的可信度已经是他观点的明证了。
对于学术界的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似乎没有任何必要的理由让一个人因为对神学或文化问题的信念而致使其无法获得一个大学教职。(糟糕的就业市场可能是另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更有甚者,像楚曼、我、乐马可、马斯登和其他学者都发现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其实都愿意出版我们在宗教史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符合在那里出版必须达到的正常学术标准。我确实遇到过来自未来雇主和出版社及期刊的匿名读者所给的微妙或公开的反基督教偏见,但我不相信在所有领域或努力中,一个人的信仰本身会阻碍你的学术成功。
正如楚曼指出的那样,当你表达的观点被主流世俗学术界认为是可憎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几乎不仅限于传统基督徒。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取消了芝加哥大学地球物理学家多里安·阿博特(Dorian Abbot)的讲座邀请,因为MIT对他批评了目前学术界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规则感到失望。由于教职终身制的存在,这种情况很少导致解雇,但大学仍然可以让那些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生活困难。
职业生涯早期、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可能会意识到,他们最好不要(或不想要)就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发表意见。当然,当你的研究与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直接相关时,这就变得更加困难。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家马克·雷格纳斯(Mark Regnerus,天主教徒)因为敢于在2012年发表研究报告,对同性父母抚养的孩子的成长提出质疑,而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骚扰、羞辱和调查运动。但他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因此在这场风暴中幸存下来。
然而,在许多领域和主题中,一个人的信仰或个人信念不见得必然引发文化战争的争吵,例如楚曼1994年经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路德的精神:救恩与英国改教家,1525-1556》(Luther's Legacy: Salvation and English Reformers, 1525-1556)。人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基督徒从各宗派的角度撰写宗教历史,还是能够在牛津或耶鲁等顶级世俗出版社找到出路的(马斯登在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爱德华兹传记)。
对于那些(如多里安·阿博特)在其他方面的观点为主流学术和媒体利益所厌恶的人,出版社和期刊有可能停止出版他们的作品吗?当然,而且肯定已经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了(至少是巧妙地)。但只要传统主义者和其他有世俗社会所不喜悦观点的人仍然可以在世俗顶尖出版社出版著作,他们就应该这样做。对许多基督教学者来说,有专门的基督教出版社支持他们也是很有必要的,很少有世俗出版社愿意出楚曼的《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谢天谢地,一些基督教出版社,如十架路出版社仍然愿意!)。
但一些基督教学者仍然能够在世俗学术界精英当中保持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他们有机会的时候在世俗媒体上发表文章。只要仍有可能,长期以来的基督教传统就是继续这样做。爱德华兹、巴文克和路易斯等基督教知识领袖都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精英学术界保持着独特的基督教声音——尽管每个人所处的工作环境都比我们的文化更加“基督化”。
一个整全的基督教学者最好在学术界作为基督教学者继续存在,只要保持这个位置不需要在神学和文化上做出妥协。我们可以为之祷告,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我们的文化表面上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宽容原则的承诺可以为基督教知识分子在主流学术文化零星角落里的见证打开大门。
上帝几乎不需要我们的学术贡献来建立祂的国度。但从保罗在亚略巴古的护教直到今天,一直有基督徒的声音在学术界的小树林里捍卫着福音真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我们在我们这一代继续进行这种见证。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Carl Trueman and the Evangelical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