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经常阅读教会方面的书籍,你会发现,一些基督徒作者热衷于谈普世教会,另一些则更关注地方教会。
两派的人都会反对这种划分,他们会说:“不,不,我也谈地方/普世教会。”但我指的是侧重点——这种偏重会体现在讲道时长、文章篇幅,甚至连感叹号的使用频率上。
从杰拉德·布雷(Gerald Bray)的新作《教会:神学与历史视角》(The Church: A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来看,他显然属于前者。在书的后半部分,尤其是在提出建议的章节中,他反复抨击宗派特色和神学上的“吹毛求疵”。在布雷看来,当今教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分裂。
而我这样的人,大概会被布雷认为是有点太注重宗派了。不过,我想说的是,甲之吹毛求疵,乙之适度修剪也。
不过,这确实是一本好书,值得我用两篇书评的长度来分享我的看法。一方面,布雷的著作值得概述;另一方面,我也想指出像他和我这样的人之间更大的差异,以及双方立场各自可能带来的隐患。我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帮助读者了解《教会》这本书的特点,同时也是对布雷的公平对待,当然,我也要坦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先说第一部分,算是第一篇书评——概述。《教会》是否属于神学院书店的系统神学部分或教会历史部分?答案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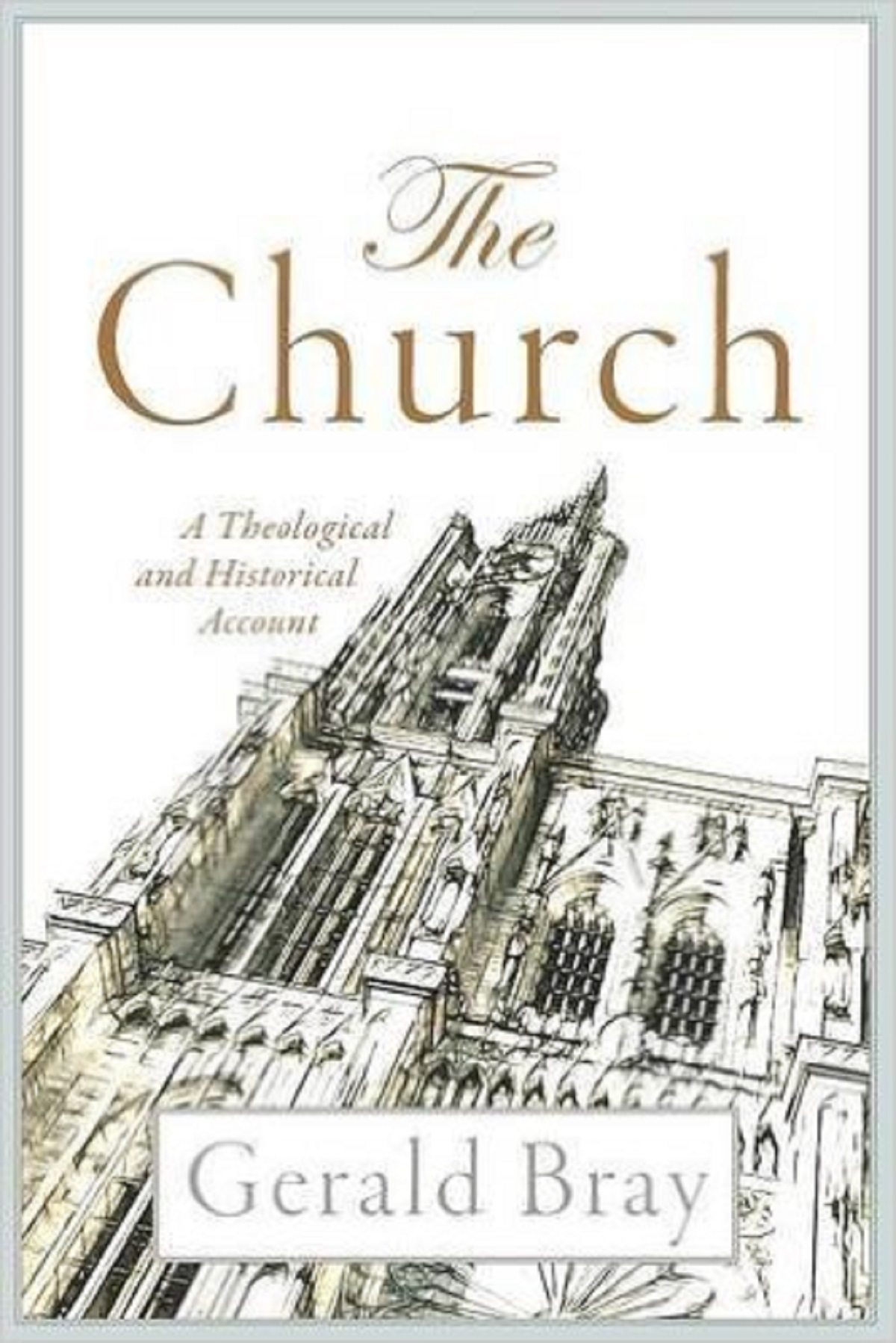 《教会:神学与历史视角》(The Church: A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教会:神学与历史视角》(The Church: A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杰拉德·布雷(Gerald Bray) 著
贝克学术出版社(Baker Academic),288 页
这本书读起来像一部历史著作,它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两千年的教会历史。第一章探讨犹太教和旧约的渊源,第二章研究新约教会,第三至六章则依次讨论了遭受逼迫时期、帝国时期、宗教改革时期以及改教后的教会。
虽然本书行文像历史书,但它的目的是阐述教义并提出建议。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本关于教会教义的著作——用神学院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教会论”。在讨论宗教改革之前的章节,每章结尾都有一个小节总结教会教义的要点。而之后的章节则探讨了基督教世界的教会论是如何在宗教改革后,像三角洲中的河流一样分散开来。最后一章(第七章)则就如何制定教义和教会实践提出了建议。
作者布雷既是圣公会牧师,也是比森神学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的教授。他在全书中都以教会的四个传统标志——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使徒性——来阐述他的教会论。举例来说,在宗教改革之前,“合一性”被理解为制度层面的统一,“使徒性”则被认为取决于主教的传承。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这两个概念都发生了变化:“合一性”转变为属灵层面的合一,“使徒性”则转变为教义方面的传承。
总的来说,这本书讲解教会教义的方式,不像化学教科书那样按部就班——先给出正式定义,然后逐条列出各个章节要点。读起来反而更像是一场关于新话题的整夜长谈。在阅读过程中,你会了解到许多有意思的历史知识:比如居普良(Cyprian)是谁?教会法是什么?弥撒、忏悔和炼狱等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新教特别重视信条?但作者提供这些历史知识,是为了引出更深层的教会论讨论:教会是新以色列吗?旧约的以色列是否就是旧约的教会?改教家们是如何看待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的?教会的圣洁性究竟是什么?
布雷指出,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神学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建构教会教义。这是因为他们既要区别于罗马天主教,又(很快)需要彼此区分,所以必须为他们共同的组织生活下个定义。布雷甚至认为教会教义是宗教改革的“核心”(第 165 页)。对于像我这样比较“宗派化”的新教徒来说,这种说法可以有两种理解:他是在说福音本身在宗教改革中并不是关键的争议点,因为双方都持有福音(如果是这样,我不同意)?还是说教会教义预设了特定的福音,所以谈论一个就等于谈论另一个(这点我同意)?这一点我也拿不准。
说到这里,让我多说几句,因为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整本书对罗马天主教的地位,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否在福音上合一这个问题,显出异常的——或许是刻意的——沉默。这其实是把历史叙述和教义阐述混在一起的风险所在。因为我们很难分清,作者什么时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说话,什么时候又是以神学家的身份发言。
作为历史学家的布雷把罗马天主教视为基督教传统中的一支——从历史和描述的角度来说这很合理,就像人们出于纯粹描述的需要会提到摩门教或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一样。但作为神学家的布雷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又是什么呢?这一点并不明确。他表达了对教皇制度的异议,也指出罗马天主教在马利亚永贞等新内容上“背离了使徒性”(第 241 页)。但他会不会认为罗马天主教已经背离了使徒的福音呢?对此他并没有明确表态。
我之所以在这个细节上多费笔墨,是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在普世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光谱中定位《教会》一书,也揭示了本书最关注的问题。
当布雷审视那些自称为基督教的群体时,最令他担忧的是宗派的混乱。他认为,坚持自己的宗派特色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基督徒合一最难以体现的地方,就是在宗派架构和事工层面”(226 页)。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在这里我想布雷指的是像我这样的浸信会信徒和保守派路德宗信徒——采用的信仰告白“声称是基于新约,但实际上通过坚持某些特定立场(比如关于洗礼的立场)而超出了圣经范围”(241 页;另见 224 页)。不过,威斯敏斯特传统的信徒也难辞其咎。他们的神学家知道“他们的宗派立场过于僵化和排他”,不得不为“他们明知最多只是次要的信念”辩护。但他们仍这样做,是因为“许多保守派担心,一旦开始修改像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样的历史性信仰宣言,就不知道这种改动会止于何处”(241-242 页)。
因此,总的来说,“保守派新教神学家们……常常躲进夸大的宗派主义中,人为地重提 16、17 世纪的争论,或是陷入吹毛求疵的争议中”(237 页)。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布雷反复以合一作为评判各种问题和趋势的首要标准。比如,他认为女性按立的议题之所以是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它“给教会合一又造成了一次打击”(245 页)。
在布雷看来,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对基督徒在福音里的合一性和大公性的更深理解:
“新教徒,尤其是福音派信徒,能否超越这些困难,对福音的大公性有新的、更深的理解,从而拥抱一个完整的神学和社会愿景,这还是个未知数。但……这是他们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考验。”
他认为我们在当代世界的基督教见证取决于此(237 页)。只要你理解了这些(关于教会合一和普世性的)担忧是如何驱动布雷和《教会》这本书的立场,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谈到罗马天主教时,他保持沉默了。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第二篇书评。布雷对罗马天主教保持沉默,以及他对宗派特色的不以为然,帮助我们看到福音派群体中存在的一个明显分化。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所有相关人士都是持守相同福音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在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上形成了两极:一端是那些强调普世教会的人,另一端则是那些强调地方教会的人。
强调普世教会的基督徒,往往把文字和热情投入在强调福音里的“合一性”和教会的“大公性”这两个特征上。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普世教会合一的方向。他们对那些引发基督徒争论的话题(比如教会治理)以及代表这些分歧的宗派缺乏耐心。他们强调解经式讲道、教导和门徒训练的重要性,而对地方教会的圣礼持比较宽松、开放和非特定的态度。他们可能会支持地方教会及其纪律,承认教会对基督徒成圣很有帮助:“这会帮助你成长!”但这从来不是他们写书或主日学课程的重点,有时甚至感觉只是敷衍了事。(例如,布雷在最后一章专门用了一节来建议实行教会纪律,但他没有给出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指导。相反,他用整章来批评教会纪律的历来使用方式,220-221 页。)在最健康的状态下,强调普世教会的人善于把首要之事放在首位,让人关注得救所必需的事。但在最不健康的状态下,他们可能偏向普救论和廉价恩典。
强调地方教会的基督徒则在主日学课程和博客文章中,更多谈论福音对“圣洁”的呼召和忠于“使徒”教义这两个特征。他们也谈论得救所必需的事——福音,但他们在定义福音时更加谨慎(第一群人会说太过谨慎)。不仅如此,他们承认像教会治理这样使基督徒产生分歧的问题对得救来说并非“必需”,但他们认为这些事项对于把福音传给下一代仍然“重要”,而且是圣经所命令的。当然,风险在于他们在评论区讨论次要问题时,可能会忘记他们在更基本的福音上是合一的。他们强调地方教会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有益处,更是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他们也谈论讲道和塑造性的管教,但在解释圣礼和实施纠正性管教时会更加严格。如果不加节制,这一端会演变成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偏激、不健康的独立性和律法主义。
强调普世教会的人更多谈论福音中的陈述性真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强调地方教会也谈论这些真理,但更多强调基于这些真理的实践要求——我们应该做什么。
强调普世教会的人倾向于把教会定义为一个团契或奥秘的交通(借用艾弗里·杜尔斯枢机主教[Avery Cardinal Dulles]的分类)。比如布雷写道:"无论教会是什么,它的核心仍然是由那些从神的灵重生的人组成的群体"(第 216 页)。强调地方教会的人倾向于把教会定义为基督统治的前哨或一个制度(再次借用杜尔斯的分类)。因此我一再把地方教会比作“大使馆”(参见《政治性教会》Political Church [书评]),而且倾向于用制度性的语言来定义它,比如:”教会是一群基督徒,共同认同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他们定期奉主的名聚会、传讲福音\举行圣礼。”(《理解会众的权柄》Understanding the Congregation’s Authority,38 页)
强调普世教会的人更倾向于称自己为“福音派”,而强调地方教会的人则更倾向于称自己为浸信会、长老会或路德宗。
话虽如此,不同的宗派传统往往会偏向其中一方。福音派(低教会)圣公会倾向于强调普世教会;而美南浸信会和美洲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则强调地方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划分基督教出版社和各个会议。
强调普世教会的人更可能从所谓的福音派公共领域(包括书籍、博客、会议、音乐节)汲取属灵养分。而强调地方教会的人则从自己的教会或其宗派资源中获取养分。
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强调普世教会的一方会使用教会外机构,而强调地方教会的人不会使用教会外机构,但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准确。事实是,强调普世教会的人倾向于使用那些可能会取代地方教会功能的教会外机构(比如各种校园事工)。强调地方教会的人倾向于使用直接支持地方教会工作的教会外机构(比如宗派架构),但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失去接触更广泛基督身体(即普世教会)资源的机会。
这种分类只是一种思考工具,无法完全公平地描述任何一方。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但我认为,说某些作者的侧重点更偏向这一端或那一端并非夸大之辞。我相信布雷和我持守相同的福音,但我们可能相差一两个点,我偏向地方教会这边,他偏向普世教会那边。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平衡的。布雷认为他很平衡,我认为我很平衡,乐马可和克里斯托弗·莱特(Christopher Wright)也认为他们很平衡。
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更完全地顺服神的话语,更好地领受福音的真理和命令,更好地作为圣灵充满的群体和基督国度统治前哨的教会。我很赞同乐马可的平衡之道:他建议在不同宗派之间保持界限清晰但不要太高,并经常越过篱笆握手。我既需要九标志强调的地方教会特色,也需要福音联盟或为福音同心(Together for the Gospel)所确认的普世教会特质。
根据我的观察,不同的福音派群体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代际差异似乎也是一个因素(这也是我的直觉)。我认为福音派的婴儿潮一代和较年长的X世代相比他们的基要主义父母更偏向普世教会(我没有统计数据支持这一点)。但一些较年轻的X世代和千禧一代却在向地方教会方向推进。
从神学角度思考,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关键问题会推动你向这一端或那一端倾斜:你是否认为圣经为教会治理或架构提供了具有道德约束力的规范?也就是说,圣经是否告诉我们应该采用会众制、长老制还是主教制?
倾向普世教会者经常主张,圣经对教会如何组织架构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性规范。布雷再次提到:
据我观察,大多数低教会福音派圣公会信徒都承认,主教制并非源自圣经,而是早期教会的一项创新——只不过经过几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它确实有用。因此,我们不妨继续保持这种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历史实用主义者。
而偏向地方教会的人则认为,教会治理其实只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称之为社会伦理。除非你认为新约中的所有伦理规范都不适用于今天,否则我们就必须通过更细致的解经工作,来确定圣经中哪些伦理和治理规范对我们仍然具有约束力,哪些则已不再适用。
与布雷的观点相反,我写道:“某些组织事务可以根据具体环境灵活调整,但教会秩序的基本原则与福音信仰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原则都是有圣经依据的(《不要开除你的教会成员》〔Don't Fire Your Church Members〕,15 页)。我们的福音秩序(这里指的是教会的治理结构)是从福音信仰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对于福音本身,以及为了展现和护卫福音而设立的福音秩序,圣经都提供了充分的指引。
就像在我在《理解会众的权柄》(Understanding the Congregation's Authority)中所说:
福音与福音秩序之间的双向关系是一个良性循环,这个模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立场对福音和教会秩序关系的理解差异。
一个人对教会治理的立场会如何影响他在教会论光谱上的位置(靠左或靠右)呢?如果圣经确实为教会的本质和治理方式提供了道德规范,那么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顺服这些合乎圣经的架构。如果没有,我们与地方教会的联系就会变得松散。参与教会将不再由圣经的命令驱动,而是由个人对属灵需要的判断来决定。如果任何教会架构都可以,那么严格来说,只要能实现架构的目的,没有架构也可以。如果你能在地方教会之外满足属灵需要(团契、教导、敬拜和类似长老的指导),为什么不呢?这样看起来,似乎基督教真正的“戏码”是属于那些认为自己可以独立于地方教会而运作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自由人。
(很可能布雷确实认为教会架构中的某些事项是圣经要求的,比如长老是否有权柄?教会是否该施行管教?这意味着,当他反对有一个新约模式时,他可能就自相矛盾了。)
这里不是深入讨论圣经是否决定我们教会秩序的地方。但这就是为什么当布雷和我有这样的分歧时,我会说:如果你想了解教会论的历史,那么可以读他的书;但如果你想为福音派寻找教义和事工的前进方向,那就不必了。
令人欣慰的是,布雷和我都确认,我们加入地方教会最终并不是出于功用性或命令性的考虑。我们加入教会的呼召最终植根于福音的宣告。正如布雷所说,我们加入教会是因为这是“基督徒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是我们的“首要群体”(249 页)。也就是说,我们加入教会不仅是因为这对我们有益处,甚至不仅是因为这是命令,而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家人。感谢赞美主!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re You a Universal Church-er or a Local Chur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