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耶稣说过的话。但如果神所说的语言是我们难以觉察的,或者我们对祂的话油蒙了耳呢?
想象一下:我们不能明白神对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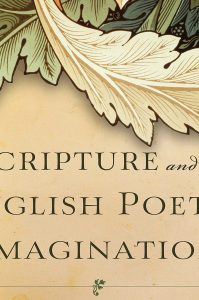 们说的话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可是耶稣警告祂的门徒,除非他们能解释比喻——除非他们能诠释比喻的讲论——他们就听不见神的启示。贝勒大学文学人文学特聘教授大卫·莱尔·杰弗瑞(David Lyle Jeffrey),在他的《圣经与英语诗意想象》(Scripture and the English Poetic Imagination)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明白神话语的钥匙。杰弗瑞说,“耶稣已经暗示了他使用虚构、比喻、奥秘讲论的目的既是为了隐藏些什么,又是为了启示些什么,如此只有那些真心寻求其意义的人才会发现它。”要听见神讲话,我们必须将耳朵调准到诗歌频道。
们说的话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可是耶稣警告祂的门徒,除非他们能解释比喻——除非他们能诠释比喻的讲论——他们就听不见神的启示。贝勒大学文学人文学特聘教授大卫·莱尔·杰弗瑞(David Lyle Jeffrey),在他的《圣经与英语诗意想象》(Scripture and the English Poetic Imagination)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明白神话语的钥匙。杰弗瑞说,“耶稣已经暗示了他使用虚构、比喻、奥秘讲论的目的既是为了隐藏些什么,又是为了启示些什么,如此只有那些真心寻求其意义的人才会发现它。”要听见神讲话,我们必须将耳朵调准到诗歌频道。
“神是位诗人”杰弗瑞提醒我们。“祂如何说话,而不单是祂说了什么,是了解祂所是的重要方面。” 因为没有留意说话的形式,一个聆听者可能会错过信息的主体。就神的话语而言,杰弗瑞解释道,“神经常像位诗人那样说话”。打开圣经,看看杰弗瑞的宣称是否正确吧:当你大声朗读圣经,有多经常听到比喻?想想创世记中希伯来文的叙述模式,诗篇中的诗歌,还有那些显而易见跳入你脑海的箴言、所罗门的雅歌,神对以赛亚和以西结诗歌体的预言,耶稣的比喻等等。考虑到诗歌在圣经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认识神部分上是基于我们对诗歌的阅读理解能力。
杰弗瑞认识到大部分读者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聆听或享受诗歌。30多年前,著名的诗人达纳·乔亚(Dana Gioia)问道,“诗歌有什么用吗(Can Poetry Matter)?”他注意到美国人有种倾向,认为诗歌是无关紧要的。“尽管还是有人写诗歌,”乔亚写道,“它已经从文学生活的中心位置上退了下来。”阅读诗歌就像阳春白雪的消遣,是住在东奥斯汀区带着贝雷帽或穿着低腰裤的纽约人研究的东西。杰弗瑞发觉人们正倾向于认为诗歌不是大众所能染指的。
但是,诗歌的高雅正是我们应当阅读它的理由。从杰弗瑞的观点来看,诗歌的考究文学风格(elevated style)强化了内容的圣洁性。由此,诗歌可能要从日常讲论中分别出来;它像是场与神秘的搏斗,倾听者抓住的是其实质的重量。“在神的国度中,为了我们敬拜在上的神,”杰弗瑞建议,“我们需要诗性的艺术:让我们能以独特的方式接近圣洁;它是信心的仆人。”就像主日是从一周中分别为圣安息的日子,好提醒我们永恒的本质,诗歌则让我们重新看见词句的重要和可畏,尤其是神的话。
《圣经与英语诗意想象》通过英语诗歌的历史,为我们描绘了方向。从乔叟到受圣经影响、以诗歌回应神的诗人安东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该书让读者一一重温。它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往日美好、不该失落的宝贝。因此,杰弗瑞的书也像一次翻拍,驶过文化的记忆,将传统中我们离开的路径向我们一一显明,由此,我们知道该如何回转。杰弗瑞说:
在我们对网络的成瘾耗尽了对美的感知力后,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未来生活,我们就需记得“以前的事是怎样的”——那诗歌还未凋零,众多廉价的小标题还未替代诗歌对心灵和头脑提供丰富滋养的时代。
杰弗瑞花了后半本书的篇幅讨论“宗教改革之后”以及在改教人文主义者中高举“自身为权威或道德例律的裁判者”的风气。当然,这些是宗教改革“意想不到的结果”,但他们深刻地影响了浪漫与启蒙运动时期作家的作品,其影响波及现代。如果我们阅读早期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诗人约翰·邓恩(ohn Donne)和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作品,我们会体验到忠心的基督徒作品,但诗歌本身却转向了个人自身。邓恩写作了忏悔诗、渴望救赎的诗歌,而赫伯特则写下祷告诗,在自己的家中将这些诗歌读给会众听并作为牧养的手段。但丁或乔叟时代的诗歌——与神学、政治紧密连结,将教会视为学院——已经渐渐被以内省为主要目的的诗歌所替代。
杰弗瑞没有花篇幅在异端邪说的浪漫派诗歌上(我的浅见,不一定是他的想法),直接从17世纪跳到了继承错误异象、以自我为参照的现代诗歌上。他引用了1953-1954年约翰·麦克莫瑞(John MacMurray)在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上的警告:
首先,现代哲学将自我作为它的起点……其次自我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自我的前提是个寻找知识的思想者,也就是寻找那些有帮助信息的人。
带着这样关于自我的预设,还会有什么人读诗歌呢?更糟糕的是,认为个体带着孤立的本性,以此为假设的诗人不可避免地写出晦涩,无意义的诗歌来。杰弗瑞认为现代主义的座右铭简而言之就是:“对你而言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诗歌从潮流中落伍。就像杰弗瑞所说,“现代诗人感觉自己必须在任何公众视野之外。”如果我们是疏离的意义制造者,我们就对读者没有任何责任,对任何在上或名誉之外的事没有热情,对任何道德判断没有权威。杰弗瑞哀叹道,“现代诗人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听众知道的词汇越来越少。这进一步切断了与过去的对话。”
但是在现代诗人中间,在当代英语诗歌中仍有盼望。那些寻找表达“个人性作为一种关系”的诗歌,那些激发“不单是私人体验也是共同回忆”的诗歌,将带我们回到“某些共同的异象中。这样的诗歌将成为我们回家的路。”
在《图像:宗教与艺术日志》(Image: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the Arts)中,凯瑟琳·威利斯·佩施(Katherine Willis Pershey)论到,“在这个充斥着战争罪恶和汽车广告的世界中,诗歌悄然而坚定地吸引着我们去注视那些寻常的美好与终极紧要的事。”
诗歌为不可言喻的奥秘命名。当寻常的词语让人觉得像是沉闷、过热的引擎发出的哼鸣之音时,诗歌就像神的介入一般,打破了一切,以至于我们可以再次听见神是谁,我们是谁。没有诗歌的话,我们也许注定将像电脑代码那样交谈,像毫无意义的广告标语,或者像吼叫的动物一般。诗歌在受造的次序中,提升我们来到富有创造性的受造者地位上。
如果就像杰弗瑞提醒我们的那样,神是“诗人的鼻祖——是写出了世界的那位,”那我们就必须学习倾听诗歌。否则我们就成为耶稣所警告的那群,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的人。
译:EYZ;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Christians Need a Poetic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