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议的那样,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读者“让这几个世纪以来干净的海风吹过我们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译注)。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接下来要审视一些可能被遗忘、但是依然和现今的教会相关,并且能帮助今日基督徒的经典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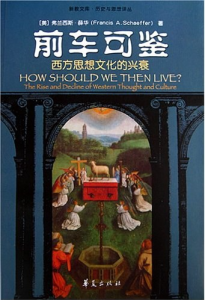 1976年,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福音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在基督教世界里活跃地发挥着影响力。当时福音派世界那些极具影响力的领袖们似乎开始用越来越充满盼望的眼光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1960年代思潮带来的充满紧迫感的文化危机似乎已经陷入衰退。
1976年,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福音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在基督教世界里活跃地发挥着影响力。当时福音派世界那些极具影响力的领袖们似乎开始用越来越充满盼望的眼光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1960年代思潮带来的充满紧迫感的文化危机似乎已经陷入衰退。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事实却绝非如此。1973年,最高法院作出了“罗诉韦德案”的最终裁决,这给全美国都带来了影响,按需堕胎变得合法。思想界所发生的大事都为文化变迁设定了舞台,福音派基督徒们带着“我找到了答案”("I Found It")的胸针并建立了巨型教会,但与此同时,文化正在向着敌对基督教的世俗主义转变,而这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显现出来。
不过,有些人还是预见到了世俗主义文化的到来。1976年的我刚刚17岁,正面临着高中的最后一年,并试图理解我周围的世界。那时,一场护教学危机已经困扰了我几年,我需要帮助。我已经看到了很多问题和疑问,而这些问题和疑问必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爆发在美国社会的舞台上。
值得庆幸的是,我确实得到了帮助,而且是来自多方面的帮助。D.詹姆斯·肯尼迪(D. James Kennedy)向我介绍了薛华(Francis Schaeffer)的著作。于是我读了《太初有道》(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理性的规避》(Escape from Reason)和《永存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薛华的著作是对我的一种神学拯救。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在书中写下的所有内容,但我确实明白了他的主要观点,它们给了我一种理解基督教信仰如何联系周围的世界和如何回答这个世界所提出那些回答问题的方法。
当时的我在问一些非常宏大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当时的我被一个世界所吸引,两部英国电视系列片向我敞开了那个世界的大门,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系列片。一部是由肯尼斯·克拉克男爵编剧、宏伟磅礴的《文明的轨迹》(Civilisation),我一分钟都没有错过;另一部是雅各布·布罗诺斯基带来的《人类的攀升》(The Ascent of Man)。布罗诺斯基讲述的人类故事和现代科学的兴起令人着迷,但我知道他所展示的很多东西与基督信仰完全相悖。
另一方面,《文明的轨迹》不太会引起这样的警觉。当克拉克讲述西方文明的故事,并以他对绘画、建筑、文学和音乐的精湛解释来说明每一个时代时,我对每一个字和每一个画面都很感兴趣。我被迷住了,我想去看看克拉克爵士在电视上向我展示的大教堂、修道院、博物馆和图书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
但其实克拉克也在讲一个故事——一个以艺术和美学价值为中心的故事。我知道新教改革,但我还不了解克拉克男爵是在用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讲述西方文明的故事。
1976年,薛华的著作《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How Should We Then Liv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出版了。我买到的是第一批印刷的书籍中的第一本。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得很投入,因为我知道薛华也在讲述西方文明的故事。
《前车可鉴》既是一本书,也好像是一个多集的电视系列片,就像克拉克的《文明的轨迹》一样。这不是巧合。薛华在这本书中同时刻意回答了布罗诺斯基和克拉克对基督信仰发出的挑战,不过他对克拉克的回应最直接。但薛华是通过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达成这一目的的。
这本书的副标题——《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与克拉克爵士的叙事几乎完全相反。薛华并不是不同意克拉克《文明的轨迹》中每一个论点,但他确实不同意克拉克的许多论点,更重要的是薛华不同意克拉克对人类文明叙事的人文主义诠释。
这本书的英文题目("How Should We Then Live?",直译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译注)让我觉得很奇怪,直到现在仍然觉得奇怪。从英文语法上来说,它没什么错误,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提问方式。不过话说回来,薛华这个人也很奇怪,他出了名的穿搭方式看起来就好像是上个世纪从瑞士山里来的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如此。薛华和他的妻子艾蒂斯(Edith)在瑞士山区创立并指导了避难所团契(the L'Abri Fellowship),这个事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各种心怀不满和满心困惑的年轻人,向他们介绍基督的福音。奇怪而奇妙的是,薛华采用了理性的方式,借助基督教护教学所捍卫的圣经真理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当其他领袖们在忙于建立福音派帝国的时候,薛华夫妇却在接待数十名长发飘飘、智力超群的年轻人,与他们的思想交锋,同时致力于诠释他们的文化。
 我在高三的第一周,从头到尾读了《前车可鉴》。根据我13岁时开始记的读书记录,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第80本书。价格是12.95美元,当时看来是花了不少钱。我知道它值这个价,但薛华的书一开始让我感到困扰。谁的西方文明主线叙事是对的?薛华还是克拉克爵士?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确定。克拉克爵士指出,几百年来文化一直在不断发展和上升,直到现在。薛华则认为现代文化中绝大部分都是悖逆神的,并且正在消亡,逐渐丧失任何做出超验判断或主张真理的能力。他认为不断抬头的人文主义是对基督信仰的直接挑战。我当时意识到,克拉克爵士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克拉克却把新兴人文主义看作是把人从古老且顽固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的思潮。令我懊恼的是,我没有意识到克拉克文明叙事背后的预设立场。
我在高三的第一周,从头到尾读了《前车可鉴》。根据我13岁时开始记的读书记录,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第80本书。价格是12.95美元,当时看来是花了不少钱。我知道它值这个价,但薛华的书一开始让我感到困扰。谁的西方文明主线叙事是对的?薛华还是克拉克爵士?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确定。克拉克爵士指出,几百年来文化一直在不断发展和上升,直到现在。薛华则认为现代文化中绝大部分都是悖逆神的,并且正在消亡,逐渐丧失任何做出超验判断或主张真理的能力。他认为不断抬头的人文主义是对基督信仰的直接挑战。我当时意识到,克拉克爵士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克拉克却把新兴人文主义看作是把人从古老且顽固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的思潮。令我懊恼的是,我没有意识到克拉克文明叙事背后的预设立场。
在我第一次读《前车可鉴》的时候,这本书所呈现的克拉克和薛华之间的碰撞,让我认识到世界观大碰撞背后的原因,而这种碰撞成为我后来生活的核心兴趣和动力。一方面,我为自己没有认识到克拉克爵士叙事的预设立场而感到尴尬。另一方面,我知道我迫切地想了解思想、道德、艺术、文化、建筑、音乐、科学、哲学和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之间有何种交集。
薛华并没有完美地讲述我所关心的那些问题。他的一些概括过于宽泛,一些关键的细节却有缺失。后世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薛华设计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目的是要借着恢复宗教改革神学和圣经权威得以重建福音派基督教。而自由派批评者则认为,薛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福音派至今仍未从里面走出来。
我认为事实与这些评价都大相径庭。后世的福音派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在学界许多学科的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了薛华。但早在现代福音派学术得着振兴之前,薛华就已经在提出和回答最迫切的问题了。
在“世界观”和“真理性命题”("truth claims")这样的词进入福音派常用词汇之前多年,薛华就已经开始向我们介绍这些术语,并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他知道世界观的大碰撞正在进行中,他非常关心当时正在基督教和知识革命之间做决定的那一代年轻人。
薛华还认为,我们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我们对现实的道德判断和理解。当他向克拉克爵士提出文明叙事的挑战时,他是对的——即使克拉克爵士可能几乎不关心薛华是个什么样的人。薛华并不是要让克拉克爵士相信他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论述是错误的,薛华更希望基督徒明白什么是迫在眉睫的挑战。
薛华在《前车可鉴》这本书的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从历史到文化,这是一条河流。”他说的很对,有这样一种流动,基督徒需要更好地知道文化在往哪个方向流动。
薛华还写道:“人人都有预设,他们会在这些预设的基础上持续地生活,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预设。”当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还没有意识到世界观的风暴即将到来时,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认为,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和世俗世界观的预设首先在艺术和高阶文化中显现出来。他的观察很对。当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在看《荒野镖客》(Gunsmoke)、带着孩子去新开的迪士尼乐园时,薛华却在倾听和观察,因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占领更大的文化。
薛华的正确之处还在于他观察到个人和平和对富裕的追求是福音派信仰的最大威胁。他预言性地批评了基督教种族主义和滥用富裕的问题。当他看到像“罗诉韦德案”这样的发展时,他的观察也很对,他知道文化中的一些地震只是表明了已经发生的变化,更大的冲击还没有到来。
他提出的问题也是正确的。我们该如何生活呢?这问题在1976年曾让薛华如此困扰,现在也困扰着我们所有人。我们即将发现,这一代的基督徒是否能信靠并活出真正的、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现在该如何生活呢?
译:DeepL;校:JFX。原文题为"Francis Schaeffer's 'How Should We Then Live?'—40 Years Later",载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校刊》,福音联盟蒙允转载。薛华的《前车可鉴》简体中文译本(有删节)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完整的繁体中文译本由香港宣道出版社出版。